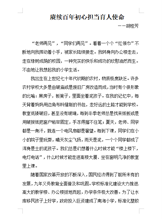“小先生”庞余亮
庞余亮 1967年生,现居江苏靖江
庞余亮 1967年生,现居江苏靖江。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小虫子》《顽童驯师记》,诗集《比目鱼》《报母亲大人书》《五种疲倦》,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躲过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等。曾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等。
1985年,师范毕业的庞余亮被分配到江苏兴化水乡深处的一所乡村学校,因为个子矮、年龄小、长着一张娃娃脸,孩子们都喊他“小先生”。
“《小先生》集中了我所有的写作才华。我写诗歌、写童话,好像都是为这本书做准备的。15年的粉笔字,15届学生的笑声,15个春秋泥操场上的露珠都在这本书中了。”庞余亮说。
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小先生》—— 一部写在备课笔记背面的“教育诗”。
中国教育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给《小先生》的授奖词这样写道:“庞余亮的《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如何理解“贤善与性灵”?你是如何将这种“贤善与性灵”诉诸笔端的?
庞余亮:一开始,我并没有写《小先生》的打算。我在备课笔记背面记下孩子们的故事,初衷是想记录下我在教学中的收获和失误。因为在老教师的课堂上,孩子们很讲“规矩”。到了我这个个子小、年龄小的小先生面前,孩子们的天性就暴露无遗。第一周我很委屈,以为是孩子们故意“欺负”我。后来我想通了,这是因为我的教学能力不够。于是我就开始记故事了。
《小先生》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生字》。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我想起了白天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喉咙里仿佛堵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紧张,惶恐,心虚。我有个优点,知错就改,而且不想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于是我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多了起来。《小先生》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继承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文心和传统,这是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我仔细想了想,这些前辈的书我都喜欢,肯定是那些“贤善”和“性灵”无意间种在了我的心里。还有,乡村孩子天生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我个子矮,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我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般转向我的方向。现在看来,那些围着我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性灵”。只要我如实写下来,我的笔端就有了贤善、性灵之光。
中国教育报:教师担负着一定的母语启蒙的任务,请谈谈你是如何对学生进行母语启蒙的。
庞余亮:我理解并且进行实践的母语启蒙是诗歌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热爱诗歌的人。在扬州读师范的时候,诗歌的影响对我特别大。做了教师,我就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讲诗歌,比如太阳不仅仅是圆的,也可能是方的;比如太阳可能是绿太阳,还可能是黑太阳;比如我还朗诵我喜欢的诗,海子的诗,孙昕晨的诗……孙昕晨有一首诗叫作《一粒米和我们并肩前进》,我的孩子们听我朗读之后,写出了很多有关米、有关秋天的诗歌。除了诗歌教育,还有童话教育,这也是母语教育中最明亮最纯粹的部分。孩子们读完童话、读完诗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他们受到了美好的母语教育,我同样也受到了教育。《小先生》这本书中就有诗歌和童话的部分。
中国教育报:《小先生》中的文章,处处充溢着爱与温情,这属于“高于生活”的部分吗?在粗粝、艰苦的环境下,以审美的眼光去观察和记录生活,需要怀抱一种怎样的信念?
庞余亮:不同人看待同一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其实再简陋的生活也有哈利·波特的9站台。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百草园。周作人看到的百草园由几棵树、几个粪坑与瓦砾堆砌组成,但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便是发现了那个通向魔法学校的9站台:“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一切都是那么迷人。很多人问,《小先生》怎么把一所乡村学校写得那么美?这美有没有存在过?我说,肯定存在过啊,而且我还见证过。晚饭花开的时候,我觉得地球的中心就在我们那所乡村学校。很多人看到的乡村教师生活是简单的,但在我眼中,那里的爱与成长是会发光的。我想通过《小先生》把那15年的光储存起来,就相当于把所有萤火虫放在一起,做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乡村生活中的“命运感”也是凸显的,在《小先生》里,有很多地方我都做了减法,当然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减去的“乌云”部分,那是乡村生活的暗影。但生活总在继续,不管快乐或者不幸,孩子们依旧要长大。这就是我无法舍去那些疼痛素材的原因,正因为有了这些暗影,乡村教育的那盏灯反而更亮了。我期待更多有心的读者,在《小先生》中既能看到灯光,也不忽略那些暗影,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乡村教育。
中国教育报:我曾经采访过一位乡村教师,她谈到乡村的寂静与寂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寂寞”这个词语在《小先生》中也多次出现——在《寂寞的鸡蛋熟了》中你写道:“要紧的是乡村那排不尽的寂寞,尤其是乡村学校夜晚的寂寞。”“我和我的十八岁走进了乡村学校……乡村的寂寞,寂寞中的坚持。”(《晚饭花的奇迹》)作为当年的“小先生”,你怎样理解乡村教师的寂寞?又是如何与这种寂寞相处的?
庞余亮: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寂寞啊,只不过寂寞的等级不一样。《小先生》是一本写爱和成长的书,但同时的确又是一本寂寞之书。乡村学校的寂寞实在太庞大了,甚至无边无际。因为孩子们下课就回家了,留下了一个有着梦想也有着痛苦的小先生。但有白天的孩子相伴,有夜晚的煤油灯相伴,有那么多的好书相伴,寂寞就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寂寞的鸡蛋”总会熟的。这样一来,寂寞就成了我最丰沛的营养。没有寂寞的营养,我就会“浮”到生活的表面,甚至会随波逐流。所以,我想对那个在学校寂寞的生活中默默写作和教书的小先生说一声“谢谢”,感谢他的坚持。
庞余亮:1985年9月7日,星期六,我监督孩子们把教室打扫干净,课桌排列整齐,然后锁上教室门,正在想我教师生涯的第一个星期天怎么过,有个老教师隔着窗子叫我,让我赶快去校长室。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可能是那个生字的问题,也可能是班级管理的问题。没想到,校长跟我说的却是另外的事情:“到了下周二,也就是9月10日,是我们的第一个教师节。”校长说到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眼睛是发亮的。校长说:“你是最小的教师,又是正宗的硬本子的教师,乡政府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你代表新教师在乡政府礼堂发言吧。”校长看出了我的胆怯和紧张,就说:“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就当那些台下的人是一棵棵树。从今天起,你就练习对着树发言。”当天晚上,发言稿的写作很顺利,写完了,我走出宿舍,看着校园里的树,想把发言稿读一遍,但怎么也开不了口。第二天早上,校长肯定了我的发言稿,还表扬我的字写得好看。校长的表扬并没有减轻我的紧张。白天我把发言稿背熟了,到了晚上,我走出宿舍,在刚刚升起来的月亮下,对着一棵合欢树背我的发言稿。教师节那天,在简易的乡政府礼堂,我代表新教师发言,只记得整个会场非常安静。会后,校长笑着说:“想不到你的嗓门那么大!”那次庆祝大会发了两只带盖的瓷杯,我到现在还记得茶杯上的青龙图案。
庞余亮:16岁那年夏天,我糊里糊涂上了师范。两年的师范生活一晃而过,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到了兴化。上师范的收获,就是让我疯狂爱上了读书和写诗。我那时还不太懂分配到乡村的意义,就觉得有拿工资的地方了。当时坐了很长时间的船才到达我即将工作的学校,那里没有公路,四面环水。那时候我还不会做教师,第一节课,我捧着粉笔盒往教室走,一位老教师轻声叫住了我,伏在我的肩头,帮我扣上了衬衫的全部纽扣。他没有说什么,但我一下子懂了,我是做教师的,我应该有个教师的样子。
中国教育报:《小先生》一书自序的标题是《请孩子们多多关照》,充满了对儿童的尊重。从你的许多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这样的童年视角。你是如何理解童年的?
庞余亮:我喜欢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爱的教育》。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乡村教师有着其他行业难以体会到的惊喜。学生们在老教师面前一点儿都不活泼,但在我的课堂上,他们总喜欢把积压的调皮和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心中,我可能更像一个喜欢读书、喜欢给他们读诗、陪他们踢足球的大哥哥。他们把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送”到我面前。童真和童趣实际上是人生的原点,忘却原点的人就像一条河水由清澈变得浑浊。我喜欢拥有童年的孩子们,喜欢孩子气,喜欢用孩子的童年校正自己人生的准量。我很庆幸当年能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教书、阅读和写作。虽然清苦,但规矩少些。孩子们像原始森林一样为我的生活提供了养我性命的新鲜空气,这也成了我的儿童观。
中国教育报:“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不再是我们村庄的人,而是一个远方的人。”“‘乡村暴力的种子’一直没有在我身上生根发芽。这个奇迹的发生,首先要感谢读书,是愈来愈多的好书,让这颗‘种子’没有了生长的机缘。”你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读书对你的影响。请问阅读之门是何时向你开启的?对你的成长产生影响的有哪些书?
庞余亮:11岁那年,我躲在草垛里用两个小时看完了从本村同伴那里软磨硬泡借来的《青春之歌》。囫囵吞枣、连蒙带猜,看完这本书的结果有三个:一是挨打了,二是全身都是草垛里的虫子咬的斑点,三是我的身体既不疼也不痒,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爱上了读书,也就爱上了写作。虽然在基层写作是相当艰难的事,虽然我们面前是平庸而重复的生活,虽然文学之路是一条比羊肠小道还坎坷的道路,但是文学所拥有的拯救与宽容的力量,远远大于生活的艰难。因为没有更多的绿化经费,爱美的老教师就带着我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红的黄的晚饭花。晚饭花开了,就意味着要放学了。然后,晚饭花就成了我的学生,我的读者,我的伙伴,我就捧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对着晚饭花朗读,这是一本我读了不下50遍的书。汪曾祺先生那些有晚饭花香的文字,就这样一颗颗种到我的生命里了。除了汪曾祺,留在我生命中的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中国教育报:15年的乡村教师经历,使你的生命有了哪些不同?对你的阅读、写作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庞余亮:我学会了等待,学会了积累,同时也学会了耐烦。我从一个急脾气的小个子,变成了一个慢性子的小老头。我还学会了尊重文学。我们每个作家的生活素材就那么多,如果匆匆写就,我觉得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有28万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觉得不满意,继续修改,并在修改中更加理解了文学的辽阔。为了无限接近这种辽阔,我的修改时间变得很漫长,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从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事实上,这样的积累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教育报:你的作品涵盖散文、诗歌、小说等不同文体,你曾说,当教师的15年,也是完成各种文体的自我训练的15年。请具体谈谈训练的方式和过程中难忘的事件。
庞余亮:对我来说,各种文体似乎没有任何障碍。文学首先是自娱,然后才娱人。当我喜欢写小说,那我会一头扑进小说中。当我需要写儿童文学,那我会一头扑进儿童文学创作中。这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年轻时要完成足够的自我训练。在最寂寞的青春时代,我一直在训练自己,我相信“1万小时定律”。寂寞其实不是惩罚,也许是命运的恩赐。1985年8月,我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前,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就得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投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因为我父母均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乡村学校也没有藏书,因此当老师后,我把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在阅读中我学会了对我所爱的文学作品进行“拆解”和“组装”。就这样,在做教师的15年中,我完成了各种体裁的自我训练,我不想辜负我面前的时间和生活,更不想辜负我热爱的文学。
中国教育报:请结合自身经验,谈谈读书写作对教师成长的意义;给今天的教师提些建议。
庞余亮:教师的成长应该是持续性的。没有阅读,我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读书有两个想不到的作用:一是可以自以为非,一是可以成为自己。第一个“非”,是界限。不断通过读书拓展自己的界限,也可以带着学生一起奔向更高的海拔。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做一个校园落叶和落果的捡拾者。校园里的师生故事,写下来就是财富。积累多了,我们都会是命运的富翁。
我推荐两种我自己总结的读书法:第一种是不求甚解读书法。不求甚解不是讲态度,而是一种读书策略。当你翻开一本书,如果你不理解,那可能是你的见解、你的知识储备暂时还没达到和这本书的作者平等对话。但如果我们读完了,生命的神奇性就到来了。很多不理解的部分,会在你生命里无意中发芽生根,我们的精神海拔会在无数个不求甚解中悄悄长高。我就是这样读完了普鲁斯特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和乔伊斯天书一般的《尤利西斯》。第二种是死皮赖脸读书法。茫茫书海,遇到一本好书不容易。如果你爱上了一本你喜欢的好书,就坚决不要放过它。只有不轻而易举地放过它,你才能体会到它的妙处——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收获。我曾把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读了不下50遍,金圣叹评点版《水浒传》读了不下30遍,每次阅读都有启迪,我再对照自己的创作,这样就能克服写作的缺点,获得进一步的成长。
中国教育报:你如何看待自己曾经的“教师作家”身份?对现在活跃于校园里的“教师作家”有什么要说的话?
庞余亮:作家就是作家,并没有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分,也没有教师作家和非教师作家之分。写出好作品,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唯一梦想。如果真的要提建议的话,那就是我们教师职业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定不能有“围墙”。比如偏向教学、教育,教化的味道很浓;比如简化了生活的复杂性,把素材和人物从立体简写成平面。文学是讲人性、讲命运、讲美学的,它相对于太阳下的事情来说,是月光,是梦。写月光、写梦,就得在写作的时候,回到人本体中来。回到最初的出发点,重新挖掘生活,肯定会有大的惊喜和收获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