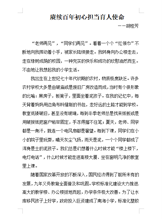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最新4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篇一
关键词:史传、史通、史学起源、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论述的诸多问题,也为后世史论家论及史学批评划定了界限与疆域,刘知所撰《史通》即从中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史传》篇也因之成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篇。
(一)、对史学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论述。刘勰在《史传》篇中清晰勾勒并描述了从黄帝时产生史官到魏晋时期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传》开篇便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1],在篇末论赞中又说:“史肇轩皇,体备周孔”。刘勰继承汉魏以来传统说法,认为自黄帝始,便存在专门记录编纂历史的史官,把史官产生时间上溯到遥远地轩辕之世,并认为到孔子时史官的各项建制已逐步完备起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巨著《史通》中,明显继承了刘勰的这种说法,在《史官建制第一》中,刘知言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2],显然是对刘勰史官起源论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
到夏商时,政府机构中设置左右史官,“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1],“唐虞流于典谟,夏商披于诰誓”。至周代,史官制度日趋完善,史官的职责就是“贯四时以联事”,即按四时,年月日时序记载事件。各诸侯国皆置史官,作国史,以成百国《春秋》。及至周平王东迁,王道衰弱,教化不正,伦常废弃,史官建制趋向混乱。“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1],开启了私人修史之风气。
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即《战国策》。西汉初年,陆贾撰《楚汉春秋》,探讨了“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的原因。司马迁“甄序帝绩”、“取式《吕览》”,列“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2],“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及至“班固述汉”,承前人业绩,创纪传断代一体先例,遂成后世断代皇朝史撰述正宗。延及三国,“纪传互出”,魏有孙盛《魏氏春秋》,鲁豢《魏略》;吴有虞溥《江表传》,张渤《吴录》,陈寿则罗列诸史,撰成《三国志》一书,因其“文质辩洽”,故使他者撰述三国之作尽废。至于晋代,“繁乎著作”,所撰史书如干宝《晋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不一而足,皇皇巨著,终得蔚然可观。
刘勰在《史传》篇中,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期间,对史官制度的变化,史书体例的演化等的描述,诠释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史学史。
(二)、对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编年体、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的两大基本体例。编年体以《春秋》和《左转》为规范,纪传体则以司马迁《史记》、《汉书》为肇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刘勰《史传》篇,对我国古代两大史书体例的优劣作了精要的论述。
对编年体,刘勰以《春秋》、《左转》为例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认为这是编年体的优点。但由于编年体是以年月日时间顺序安排史事,历史事件往往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若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定会使史事前后分离、拖沓冗长,以致出现“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的局面,损坏了史事的完整性、连续性。刘知在《史通・二体》中指出:“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但刘氏同时也指出编年体“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2],更为明确地对编年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论述。这是由编年体的体例特点所造成的。
对纪传体,刘勰认为它的优点在于“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崇焉”[1]。刘知在《史通・二体》中引申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糜失,此所以为长也”[2]。刘勰认为纪传体的缺点在于“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1],这是就纪传体记叙的互重性而言的。刘知继承了刘勰这一观点,认为纪传体“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
在《史传》篇里,刘勰第一次系统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及其著作时的困难,虽言语简略,但却极富开创性意义,为刘知在《二体》篇中详细论述二者优劣提供了先例。这种对史书编纂的思考与探索,是史学逐步走向自觉的体现,也是史学即将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刘勰《史传》篇,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发展、史书体例、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开启了研究、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潮流,也为后世诸史家划定了研究的疆域与范围。唐代刘知所著《史通》中《六家》、《二体》、《史官建制》等篇无不可见刘勰思想的影响,这便正恰如范文澜所评价:“《史通》专论史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繁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3],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梁).《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浦起龙(清).《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范文澜。《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史论文 篇二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90-02
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虽然招生来源已很广泛,一般都面向全国招生,但所招新生毕竟不能与名牌大学的生源相比,而且大多面临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应对危机,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特色专业,引导高校各专业根据自己的定位,确定个性化发展目标,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笔者认为,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与需求的变化,在高校不少专业课程纷纷探索教学特色的新形势下,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无疑也应该以追求课程特色为努力方向之一,以提高教学的质量。此处所说的课程特色,并不等于在通史课程之外设置区域史之类的特色课程[1],而是在专业通史课程中追求特色,形成特色,以特色求质量,以特色求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一、在课程内容方面,构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史内容体系,凝聚自身的内容特色
在历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课程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有着比较稳固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从初版到修订版再到增订版),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从第一版到第五版)等影响极大的教材使得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和知识系统长期稳定不变,对中国古代史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2][3],但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今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普遍依赖已经形成的既有教材和体系,有很大的惰性。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更新很难尽如人意。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仍在普遍使用几十年来一直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陈旧的内容体系,单调的教材形式,很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探索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在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以时段最漫长,内容最复杂而尤其需要构建有特色的内容体系。在这一方面,重点院校做了一些尝试,值得地方院校同行借鉴。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编著的《中国古代简史》继承了《中国史纲要》注重贯通的特点,是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师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在内容上需要做出适当的详略取舍,如以中华文明史的重大变迁问题为重点,开展课堂教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学生理解重大事件,能够分析当前的社会转型问题。其教学内容是以春秋战国社会转型、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唐宋变革、晚明社会变迁等四个重大社会变迁问题为线索贯串起来[1]240。知名院校的成功尝试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史学课程教学颇有启发。
改革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宜用一以贯之的知识线索贯串全部内容,在兼顾全面性的同时,力求知识的新颖和创见,凝聚自身特色。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史教学应顾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但很难讲好,只能在全面和重点之间折中权衡,要以脉络贯通为旨归。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而应积极吸收专题史研究成果。严耕望就认为中国通史宜以文化史为重[4]。纵观各时期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樊树志《国史概要》都是有特色的课程教学例证。
二、在课程目标方面,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本地中学历史课改实践,彰显鲜明的地域特色
除了上述将教师本人对古代通史的研究所得融入教学内容,要培育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内容特色,还应当依托当地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开展实践教学,带领学生积极研究地方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遗产,把实地考察和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当中。要将地方历史文化精华有机地融入中国古代史课程之中。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源,让地方志内的丰富资源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中国古代史课程群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探索途径[5]。
借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应该说“在当地发现历史”。随着区域史地方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几乎公认,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值得发现和挖掘,从而为理解国家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能够离开地方史、区域史的,都是由无数地方史和区域史有机整合而成。因此,我们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从史源的角度而言,其实本来就应当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每一种人群中发现和提炼历史,从而为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在地化资源。
其次,要关注地方历史教学实践,引领改革方向,努力反映地方历史教学的实践经验,增强高校历史教学的针对性。地方本科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负担着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要使命,更承担着推进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新任务。因此,必须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培养模式上的教学改革。及时地了解中学基层历史教学的现状和需要,切实改进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发挥有效服务地方教育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功能。具体来说,可以和中学联合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可以开发和编写校本教材,可以创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基地。如此方能彰显地方教育特色。
三、在课程教法方面,改进教学模式,探索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
要形成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还有必要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多种试验,在不断地试验中总结和积累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更高要求。教师必须紧跟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不断提高自身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学科水平,为此,需要开展中国古代史相关专题的针对性研究,例如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军事史等专门史学科,才能给学生以有效的专门化指导。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各方面内容的认识,让自身的知识个性在教学中逐渐彰显,从而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方法。
要探索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途径因人而异。例如充分开发和制作历史图表,利用图表进行中国古代史教学。严耕望认为,“图与表最能使读者、听者容易领会,使他们印象深刻,其功效较文字说明要强得多”[4]197。而现在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大多缺乏图表,甚至全无图表,这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加以改进的问题。既然存在这一不足,我们就可以在历史图表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普遍存在史料不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史料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历史论述比重不少,于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高校,就可以在民族史和边疆史的教学上创出特色。
在教学评价上,中国古代史课程也应该探索有特色的考核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的学业成绩考核方式向来以闭卷考试为主。这是绝大多数高校都通行的方式,其中又有考前命题制卷和建立试题库的不同做法。为了做到教学管理的规范有序,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这种考核方式方式是不宜随意改变的。但是,中国古代史教师并不是无所作为,也可以探索特色。例如在命题制卷时,可以适当地根据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精讲的研究心得制成考题,这样的考题就是颇有特色的,其评分标准也就相应的需要凸显特色。在考题类型上,可用填空题、选择题、论述题,而史料分析题尤其能够体现特色。
四、在课程对象方面,增开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为中国古代史特色教学培育新的生长点
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基本生长点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其次是研究生。一般来说,我国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数量普遍不多,但知名高校有着数量可观的研究生,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甚至是重点对象。在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实力一般较弱,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招研究生的资格,只有人数有限的本科生,因此要发展中国古代史教学,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生长点。
怎样培育新的生长点呢?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争取为全校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公共选修课程[6]。在地方本科院校,开设历史学专业的并不多,但不管有没有历史学专业,非史学专业本科生的数量都是庞大的,其中对中国古代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知名高校已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表率,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笔者不揣浅陋,也已在本校开设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三年,每学期开设,每期选修人数逐渐增多,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选课需求。在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的教学上,我们在有限的28课时之内,在专业课内容的基础上,选择有自己特色的内容,精心编写了十几讲教案,制成课件,精心教学,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总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地方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师在积极向知名高校的同行学习教学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合自身条件的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立足地方,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与地方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接轨联动,以鲜明的教学特色影响周边,辐射全国。
参考文献:
[1]彭南生。研教双优,彰显特色(第二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2]张晗。反复修订终成“不易之论”――《中国史纲要》出版纪实[J].全国新书目,2006(23).
[3]刘后滨。经典教材的生命力――评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J].北京大学学报,2007(3).
[4]严耕望。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王小健。论中国古代史的课程群建设――兼论文化人类学对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意义[J].大连大学学报,2012(5).
中国古代史论文 篇三
摘 要:新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已经成为唐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资料,也是当今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作为一类出土文物,许多大型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将墓志作为一类重要藏品。当今刊布唐代墓志的方式主要有: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研究考释类、目录索引类等等。
关键词:墓志;唐代;图版;释文;收藏;刊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43
中国古代志墓之葬俗由来已久,墓志[1](图三、十四)发展到隋唐时期,踵事增华,动辄千言,载志主姓氏f源、家世乡贯、婚姻族属、身份地位、经历生平及等,颇类正史之“列传”。虽因体例所限,志文内容叙述较史书之“列传”更为简略,两者之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且难免有浮夸虚赞、褒扬谀美的成份,但一般说来,关于姓氏、生平、官阶、年寿、卒葬、子孙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基建、考古、盗墓等因素,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为数甚众,作为不断涌现的中古史研究“新资料”,唐志材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受到学界的重视,不论是公私博物馆,还是个人,均有不少致力于唐代墓志的收藏和刊布。关于唐代墓志的收藏,除了由正规考古发掘而得,并由考古单位收藏的原石之外,还有一部分公私博物馆是通过征集、购买、调拨等途径收藏唐志原石,大部分的个人限于财力及观念,主要以墓志拓片的收藏为主。今天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界还是收藏界对唐代墓志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就其刊布的形式而言,大体延续上世纪的几种方式,主要可分为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编目索引类、零星考释类等等。
1 释文类
此类以汇集墓志录文为目的,将一定数量的墓志录文汇集成编,极便学者在研究中阅读及使用,以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2000年)、第8辑(2005年)、千唐志斋新藏专辑(2006年)、第9辑(2007年,主要收录的唐代石刻资料以山东桓台县拿云博物馆藏唐代墓志数十方为主)[2]。还包括《全唐文补编》(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①亦收录了一些唐人墓志。此类图书已经将墓志录成文,故而省却了学者在研究中自己录的“工序”,但是其缺点亦显而易见,主要有两点:其一,因为没有附刊拓片或原石图版可资对读,录文的质量也只能依赖释读者的水平,假如释读有误,研究者往往只能因错就错,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二,如《全唐文补遗》诸卷,大多没有交待志石原藏地,或者拓片来源,除了无法对录文进行复核,又限于编撰体例,无法如实的反映墓志的原生形态,也可能因此丧失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志上的花纹(图四)、志文的行款、文内的平阙式、志与盖的撰书者题名等等。
2 图版类
顾名思义,即只刊布拓片图版,无文字释读,现在收藏界有不少专以石刻拓片为主的收藏者,在刊布私人收藏时,以此种形式为多。其优点是大致保存了墓志拓片的原貌,其缺点是学者在研究中需要花M更多的时间去释读和校正文字,限于书本的篇幅,有些大幅的墓志只能缩印,亦会给释读带来一定困难。其中洛阳赵君平、赵文成二先生集中刊布新出墓志的《邙洛碑志三百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L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图八)“四部曲”最为重要。此外,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3](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所收录的拓片均为齐运通先生的个人收藏,大都字口清晰、墨光灿然,加之编者常年在文博系统工作,对石刻、拓片有独到的研究,书末附录了墓志边饰,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3 图文对照类
此类集图版与释文为一体,堪称墓志资料整理的最佳模式,更为符合当代的学术规范。当代较为大宗的唐代墓志刊布时大多采用此种形式。如《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延续《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李献奇、郭引强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编纂体例,刊布考古发掘所获的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各地方文物机构编辑《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丛书②,分省刊布1949年解放后出土的全部墓志材料,唐代墓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有《陕西〔壹〕》(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0年)、《河南〔贰〕》(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2年)、《重庆》(中国文物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编,2002年)、《陕西〔贰〕》(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3年)、《北京〔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馆编,2003年)、《河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2004年)、《江苏〔壹〕・常熟》(中国文研究所、常熟博物馆编,2006年)、《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2008年)、《上海、天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2009年)《江苏〔贰〕・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2014年)、《陕西〔叁〕》(故宫博物馆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1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力光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则刊布了西安碑林博物馆1980年至2006年间新入藏的历代墓志,以唐代墓志为主。《长安新出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收录了西安市长安区经考古发掘等途径所藏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唐代墓志仍是主体。历代墓志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众多收藏品中的大宗,至今的收藏已经超过千种(图二、十一),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的五百方,由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整理出版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因为本书的录文出于大量优秀的唐代文史研究者之手,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是当代墓志整理的代表作。《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毛阳光、余扶危编,201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2000年以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300余方,每方都有释文和标点,著录其尺寸、书体、行款等信息,配以拓片图版。《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5](赵力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刊布了《汇编》出版之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的历代墓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是全国一部由文物稽查队追缴墓志汇编而成的石刻文献图书。《珍稀墓志百品》(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则是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在自己收藏的墓志拓片中精选了100种,有不少是第一次刊布。正如胡戟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些墓志流散之后,原石已经不知所踪,作为拓片的收藏者,有义务让学界及时了解这些流散中的墓志资料。
4 编目索引类
及时且系统地掌握新出唐代墓志相关信息,从而有效的依托新出唐代墓志资料展开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学界急需有关新出唐代墓志数据的编目索引类成果。在这方面,由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编纂,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唐代墓I所在t合目h》[6](1997年)初版以来,已经成为唐代文史学界检索唐代墓志最为常用、最为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活跃唐代石刻墓志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墓志的不断刊布,继续追踪新见唐代墓志资料的刊布与整理,两度增订再版:《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2004年),《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订版)》[7](2009年),据最新修订版前言,其收录范围为2008年年底之前公开发表的唐代墓志,总共收录唐代墓志、志盖8737方,其中志盖369方,较2004年版《新版目录》新增1909方,其中志盖1方。高蚓@男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石刻相关图书,已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2009年)[8-9]、《中国石刻vS目h(2008-2012前半)稿》(2013年)两书对于从事中国碑志石刻研究的学者把握学界前沿亦有功用。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陈尚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一书,“是至今为止编录唐五代文章最基本的几个系列图书的作者索引”,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出自唐人墓志,故为检索唐人墓志大有裨益。《〈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吴敏霞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是对《全唐文补遗》前九辑的内容编制了索引,按照所收录的墓志,提供了全套书的总目录,极便学者使用。中国学者陈尚君[10]、王素[11]、仇鹿鸣[12]等有专文对近年来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总结。
5 研究考释类
除了上述石刻专书中所刊布的大宗新出唐代墓志外,还有不少在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各类学术期刊中刊布的唐代墓志,其中有关新见唐代墓志的专集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刊布了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墓志46方,并对墓志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考释。第二种,杨作龙等主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3],全书共分三编:一、墓志研究与考释,收录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整理和研究,共收录论文15篇;二、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对32方墓志进行了整理;三、新出土墓志目录,其中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唐志140方。第三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多篇专题文章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内容涉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均为初次刊布,学术价值重大。第四种,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收录各类墓志考证文章约20篇。以新见单方唐志的刊布与研究为目的,在《文物》《考古与文物》(图九、十二)《唐研究》《碑林集刊》《唐史论丛》《出土文献研究》《书法丛刊》《中国书法》《文博》《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乾陵文化研究》等杂志刊布数量日益增多、速度日益加快,尤其值得唐志及唐史研究者关注。
除了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外,因地域不同,材料所限,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中古时期的大量砖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共同刊布了新、旧吐鲁番出土唐时砖志,为数亦不少。
荣新江先生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中,列有专讲谈石刻史料,从传统的石刻文献、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石刻数据目录等方面总结了石刻史料―“现在史学研究所不可不予理会的文献材料”[14]的收集和利用问题,指导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如何有效的利用石刻史料,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 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A].赵力光。碑林集刊(12)[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328-335.
[3] 陈尚君。《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2):1-10.
[4] 胡可先。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J].北京大W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2-48.
[5] 仇鹿鸣。《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2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54-560.
[6] 刘建明。《唐代墓I所在t合目h》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51-557.
[7] 仇鹿鸣。《新版唐代墓志所在t合目h(订版)》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99-603.
[8] 仇鹿鸣。《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书评[A].荣新江。唐研究(1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33-639.
[9] |山智史。《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书评[J].唐代史研究(13),2010:127-136.
[10]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A].陈尚君。贞石诠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6-37.
[11] 王素。近年以来魏晋至隋唐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J].唐代史研究(5),2002:87-105.
[12] 仇鹿鸣。大陆学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2007-2010)・石刻[A].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253.
[13] 毛阳光。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5-27.
[14]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38.
中国古代史论文 篇四
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9月18至21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工作以及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的颁奖活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全额资助并承办。本届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论文91篇,获奖论文为36篇。为保证本届论文评选活动更加合理与公正,评委会制定了更为严密的评分标准、工作细则及避嫌制度。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陈迎宪处长在致辞中指出,本届论文评选,无论从程序方面还是评委组成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颁奖仪式后,由戴嘉枋教授和学会副会长修海林教授分别对本届论文评选的近现代和古代部分进行了点评。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参赛论文的水平在逐年提高。戴嘉枋指出,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部分的参评论文其优点在于选题有较大的开拓,史料工作扎实细致,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有所拓展。当然问题也有一些,如有的选题比较粗浅,有的文章内容与音乐联系不够,还有的文章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不够到位等。古代史方面,修海林指出,在方法论层面,一些作者对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有意识去掌握和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彰显了论文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不足之处在于有的文章缺乏理论高度,有的文章对中文摘要和结论重视不够,有的文章题目与内容不是很吻合,还有的文章选题过大等。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研讨,主要围绕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史教学及研究等几个议题展开。
古代音乐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乐律学等领域。音乐考古学方面的文章如《青铜音乐的辉煌――写在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之际》(王子初)一文配合光盘《曾侯乙编钟》(王子初主编、出品),全面直观地介绍了曾侯乙编钟这一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音乐科技成就。音乐考古学领域的文章还有《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田可文、李虎)、《再谈甬钟的起源》(王清雷)、《春秋中期甬钟的转制》(王友华)、《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的回顾与展望――兼回李玫女士》(李荣有)、《北朝佛教遗址中的乐舞壁画研究》(乔晴)等。乐律学方面的文章多富创见,如《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郑荣达)一文认为康熙十四律,既不是没有规律而“紊乱无序”的,也不是“清制平均十四律”,而是有序而规范的“三分损益十四律”;《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谈“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方法的并存》(修海林)一文指出,从最新出土的放马滩秦简《律书》中记录的“公约数”表明,先秦十二律三分损益计算方法应该具有“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计算方式。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还有《中国古代工尺谱的变迁》(郑荣达)、《“引商刻羽、清角流徵”研究》(丁承运)、《关于中国古代应用律学理论研究的思考》(郭树群)、《明清以来“宫调声情”理论的阐发与实践》(吴志武)、《宋代唱赚谱一个谱字的解释》(杨善武)、《平调考》(成军)等。音乐文献学方面的文章有数篇,有的具有开创意义,如《关于(二十五史音乐志)辑著的汇报》(刘蓝)一文中介绍了作者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宋代古琴音乐研究暨宋代古琴文献史料汇编》(章华英)一文对宋代古琴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辑佚、校注,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古代音乐史方面的文章还有《珍贵的清代音乐史料――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齐易)、《中国古琴谱字乐符字典前言与凡例》(王德埙)、《古乐复兴之余波――汉宋之争与清代音乐史学思想之嬗变》(黄敏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之探微》(丁同俊)、《清代西传时调小曲初探》(李冉)、《(汉书・艺文志)之(乐记)非(礼记)之(乐记)》(聂麟枭)、《先秦音乐自然观的若干问题探索》(刘宇统)、《北京宫廷音乐之元代宫廷乐器简述》(崔竞源)、《谁家玉笛暗飞声――从唐代诗歌对笛子的描述鸟瞰唐代笛子艺术的发展》(王瑜)等。
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部分,在选题和史料方面均有较大拓展和突破。汪毓和先生在大会发言,畅谈《对编印出版作曲家“全集”的认识和工作体会》,对诸多学者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洛秦在《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对目前的史学理论提出反思;《个案研究――以陈洪为例》(李岩)一文对陈洪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陈其射)一文通过弘扬王光祈学术精神,希冀促进我国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近代现、当代音乐史部分的文章还有:《从近年发表在国内音乐杂志上的文章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李淑琴)、《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家研究》(李晓天)、《谈(燕京学报)上的中国音乐史学论文》(陈勇)、《谈音乐史学的创新》(王誉声)、《由(女高师周刊)全新解读女高师音乐系》(祁斌斌)、《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林苗)、《俞逊发笛子音乐艺术研究》(张平、纪维剑)、《移居香港的大陆作曲家研究――“二十世纪港澳台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进展情况汇报》(高洪波)、《“春蜂乐会”考》(杨和平)、《民族管弦乐在香港的传承与流变》(彭丽)、《吕骥战争时期的传统音乐理论实践活动》(魏艳)、《赵松庭笛子艺术研究》(寇永春)、《角色转化双向同构――试析地方艺术科研机构与属地高校艺术院系共建关系》(裴小松)、《20世纪早期哈尔滨音乐活动的俄文资料考究》(胡雪丽)、《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胡斌)等。
本届年会,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文章较少,需要引起关注。郑祖襄在《研究生“配餐式”教学的利和弊》一文中对研究生的教育方式提出反思;李方元在《传统与现代: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与学的思考》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育与研究,一方面继续借鉴现代学术的成就,另一方面还得加强与传统学术的联系。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文章还有《古乐史教学中的“注”“译”“记”――以与先秦琴之演奏相关的三段文献为例》(王洪军)、《时空观念的统一:有关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几点思 考》(康瑞军)、《有关师范院校中(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意见》(国华)、《地方院校音乐学专业的中国音乐史本科教学几点谈――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为例》(潘林紫)、《关于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高志利)等。
这届年会,还有几篇专题史以及学术批评的文章,值得学术界关注。郑锦扬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的若干进展与特点――当代音乐专门史笔记》一文中指出,中外音乐关系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兴盛的一种专门史;《台湾祭孔音乐巡礼》(赵广晖)一文介绍了台湾的祭孔音乐。该领域的其他文章还有《一个新学科的崛起――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史研究》(冯兰芳、孟维平)、《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徐元勇)等。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界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掌握批评的原则与尺度,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回忆我的一次学术批评》(刘勇)一文以作者曾经的一次学术批评为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反思,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这种敢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以己为鉴的行动令人钦佩,给人启发。
按照学会章程,本届年会还选举出了新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鉴于目前史学会会员已经近500人,经上一届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新一届理事会名额由原来的29名增加到35名,常务理事会名额由原来的7名增加到9名。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名):丁承运、王子初、王清雷、方建军、田可文、冯长春、刘勇、刘再生、刘镇钰、刘明澜、孙晓辉、张静蔚、李方元、李岩、李玫、李幼平、杨善武、陈荃有、陈其射、陈秉义、孟维平、郑锦扬、郑祖襄、项阳、赵维平、赵为民、洛秦、郭树群、修海林、高兴、陶亚兵、梁茂春、章华英、喻意志、戴嘉枋。新一届常务理事会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名):会长:戴嘉枋,副会长兼秘书长:修海林,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清雷、陈荃有,副会长:王子初、郑祖襄、郑锦扬、洛秦、梁茂春。
闭幕式由学会新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修海林主持。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才君教授致闭幕词,学会新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修海林宣读新一届理事会名单;新任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清雷宣读I OO多位新入会会员名单;上一届学会会长王子初和新任会长戴嘉枋先后发表重要讲话;副会长郑祖襄对年会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学会副会长、厦门华侨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郑锦扬表示将承办下一届年会。
王清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众鼎号为大家整理的4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能够帮助到您,是众鼎号最开心的事情。